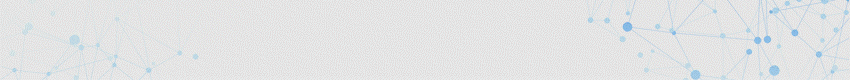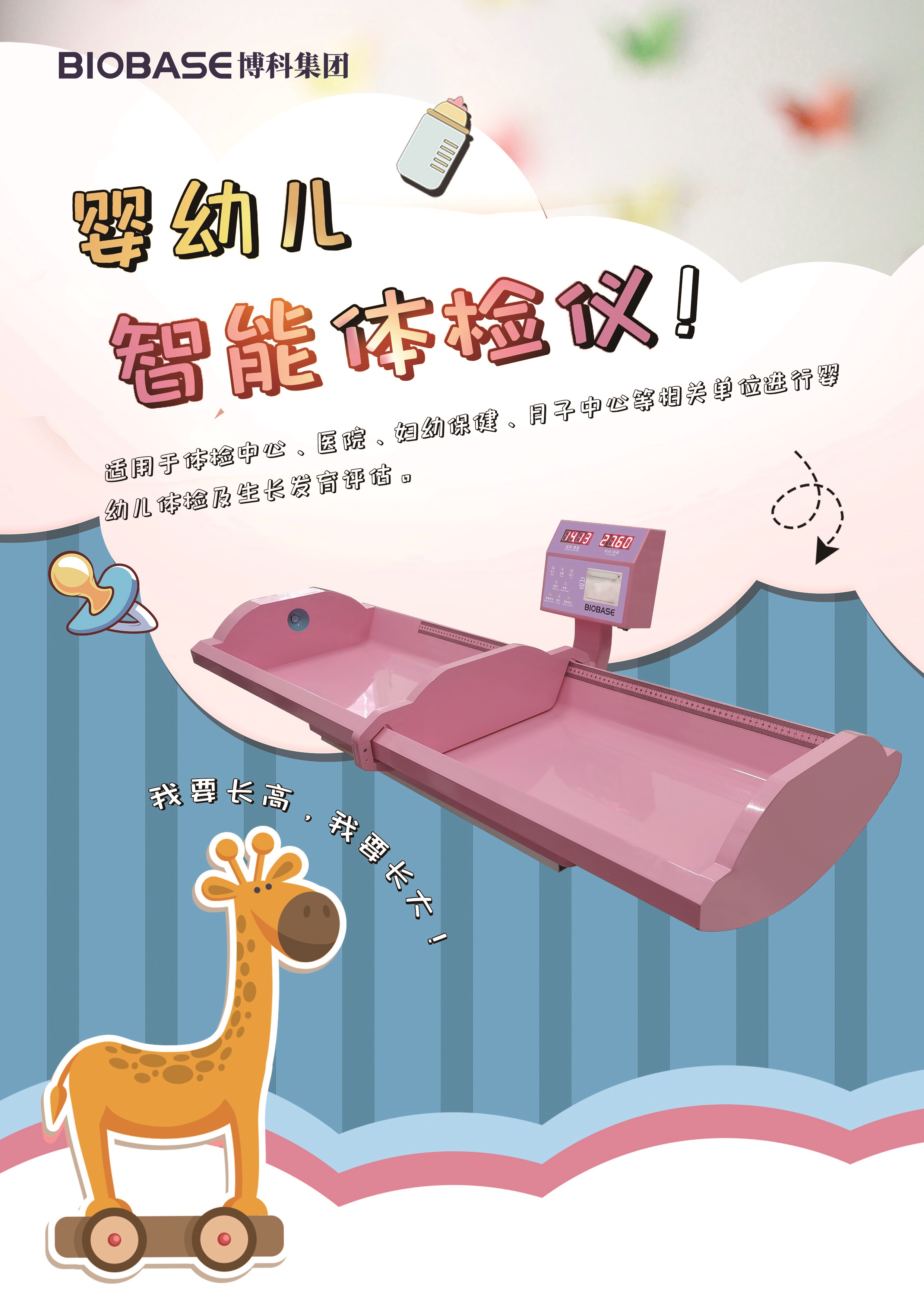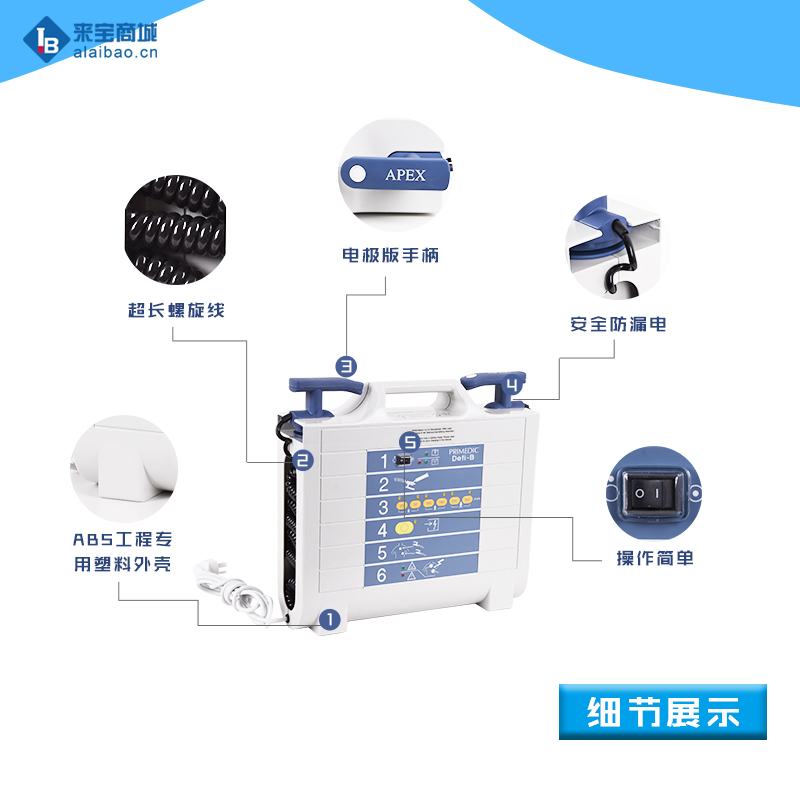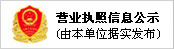生物技术与国际法
- 来宝网2007年8月5日 15:51 点击:1908
生物技术也称生物工程,它以生命科学和技术的理论与成就为基础,将之应用于生物体的生长与加工过程,有目的地对生物体进行控制和作用,从而提供人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近20年来,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和成果,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疾病诊断、治疗、预防方法和新的医药。人类基因的解码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新高峰,生物技术可能会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医学进步的新时代。生物技术的运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从人类到动物,从基因到病毒,从植物到树种,都已经为生物技术所涉足。生物技术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逐渐显露,相应的法律问题也提了出来。
药品的专利问题一向有争论,生物技术产品专利问题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核心问题是,生物技术产品是否有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即,它是否符合申请专利所需要的三个基本原则:实用性、新颖性、创造性。对生物技术与专利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人体基因、生命形式是否属于科学发现
由于专利法规定科学发现不能授予专利权,因此,即使在欧美及日本也有人认为,微生物和人体基因等遗传物质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属于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前联邦德国最高法院1975年的判例“酵母”所涉及的专利申请在联邦专利法院就曾被驳回,理由是所申请保护的微生物自地球上有生物以来就有,属于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联邦最高法院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对其可以有计划地利用。生物自然力获得有因果关系的结果也是技术方案,发明如果能提供一种可仿制地生产微生物的方法,则可以对该微生物授予专利。又如,欧洲专利局1994年的异议审查决定“松弛素”所涉及的人体蛋白编码DNA片段即被异议人认为是已经存在的天然物质,属于科学发现,要求撤销其专利权。而异议审查小组则认为,分离和表达人体蛋白编码DNA片段不是发现,所申请的DNA片段是有具体结构和用途的全新产品,因而可以授予专利权。
实际上,发明与发现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如果某专利申请仅仅揭示了某微生物菌种或人体基因的客观存在,应当认为是一种科学发现;而如果能够首次将其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使其具有应用价值,则应当认定为一项发明。这样做,与专利法规对于其它天然物质的规定是一致的。仅仅发现了某一天然物质的存在属于科学发现,是不能授予专利权的;而通过技术手段第一次将其分离出来,改变了其存在状态或内部结构,从而使其显示出过去未曾显示的使用价值,就可以视为一项发明,可以依法授予专利权。现在,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都认为,人体基因是可以依法授予专利权的。
(二)伦理道德标准问题
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利法律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判断标准越来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例如,在欧洲专利局的“哈佛鼠”一案中,就多次涉及伦理道德的标准问题。在欧洲专利局异议审查合议组的公开审理中,异议人多次指出,用动物作试验和折磨动物是不道德的;而且,带有癌基因的动物一旦从实验室跑出,就会对环境造成无法控制的污染,严重地妨害公共利益。而专利权人却辩解,其发明可以减少受试动物的数量,从而从总体上减轻动物的痛苦,且高效地用于研究和开发治疗癌症的药物是为了免除人类的痛苦,保证人类的健康,因而是道德的。合议组则认为,应当综合权衡发明可能带来的害处和危险与发明的益处和优点的关系;本发明的益处是无可争议的,不能由于技术危险就不授予专利;控制危险技术的使用不是专利局的任务,而是其它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然而,伦理道德标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各国宪法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又涉及民法通则关于人只能作为法律主体,而不能作为客体的原则。伴随生物技术的日益发展,许多有关生命伦理学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暴露。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对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已不再是什么科幻电影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而且,人类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比如致癌化合物、杀虫剂(如DTT)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其它产品,它们都是难以纠正的灾难的根源。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人类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也承担着如何使人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另外,伦理道德标准还涉及民族、宗教、社会及文化等诸多方面,这无疑已远远超出了专利法所能涉及的范围。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应当通过国家及全社会来逐步加以解决。
(三)关于动物和植物品种的概念问题
由于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其传统生物学的繁殖往往难以保持可重复性,因此,多数国家的专利法都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然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尤其是DNA重组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各种转基因动物或转基因植物,这是立法者当时未能预料的。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植物的出现,已经从技术上克服了这种缺陷,从而对这种法律规定提出了挑战。1990年,欧洲专利局申诉委员会对“哈佛鼠”一案所做出的决定中,对“品种”一词做出了狭义的解释,将其等同于动物分类学“种”的概念,曾经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于植物品种这一概念,其解释也出现了混乱。例如,虽然欧洲专利公约和德国专利法都有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但在审查实践中已经授予了许多植物专利。欧洲专利局申诉委员会在1988年“杂交植物”判例中,认为关于植物品种没有定义,而根据某些成员国的植物品种保护条例的定义,植物品种应有稳定性和同质性,而该申请的“杂交植物”已经改变,因而不属于植物品种,可以授予专利。在德国,凡是没有列入植物品种保护条例的植物,实际上都是可以得到专利保护的。而在欧盟1998年7月6日发布的98(44EG)号指令和欧洲专利组织管理委员会1999年6月16日根据该指令所修改的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中,又一次肯定了对动物和植物品种概念的这一解释,即:“‘植物品种’指任何一个单一已知最低级别植物学分类单位的植物群体”,“要求保护的植物或动物若不限定于一个特定的植物或动物品种,就是可以授予利的主题”。
(四)关于生物体的保护问题
有关生物体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直是西方许多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它有时成为一项判决能否成立、一项立法能否通过的关键所在。分析这些国家的判例和立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问题的实质是人体及人体的部分(器官)是否可以享有独占权。目前看来,美国自Allen案后,美国专利局有关动物专利的《通告》以及哈佛转基因鼠在美国获得动物专利,随后又获得欧洲专利,以及美国《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法》议案、欧共体《理事会指令》对动物、植物,甚至动物和植物品种获得专利保护都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同时他们的判例和立法中都明确禁止人体及人体的部分获得专利权。人体本身不应获得专利权看来不存在太大的争议,问题是人体的部分应当包括多大的范围?是人体体内和体外的所有物质还是仅指人体器官?人体的部分是否也包括人类的遗传物质?从目前国外的情况看,禁止专利人体及人体的部分范围是很大的。人体的部分(parts of human body)不仅仅指人体的器官(organ of human body),而且包括人体细胞和人体遗传物质。虽然人体的部分被禁止获得专利权,但是包含人体遗传物质的生物体却有可能获得专利。比如: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合成某种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的人类DNA片断与细菌的遗传物质重组,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细菌,而这种细菌是可以获得专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转基因微生物或转基因动物享有专利权是否意味着对人体的部分也就拥有了专利权呢?另外,从技术上来讲,人类目前距有能力制造人体器官的日子也并不遥远了,这种利用生物工程技术离体制造人体器官对更换人体坏死的器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制造过程具有明显的工业生产的特征,这种离体单独制造的人体器官应当获得专利权吗?
(五)关于“微生物”的概念问题
这里所说的微生物,包括各种细菌、真菌、放线菌和病毒,动植物细胞系、质粒、原生动物和藻类。对于微生物新品种发明的专利保护,各国都已达成共识。当然,未经人类的任何技术处理而自然存在的微生物,属于专利法中所述的科学发现的范畴,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只有经过特定的分离、筛选或培养技术产生新的微生物品种,可重复获得,且具有特定的工业用途时,微生物才可以得到专利保护。此时,除该微生物新品种可获产品发明专利外,生产这种微生物的方法还可获方法发明专利。应该注意,下列两种生产新微生物方法就不能被授予专利:(1)由自然界筛选特定微生物的方法。这类方法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很大随机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重现,不具有实用性,因此,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这种方法可以重复实施,否则不能授予这种方法专利权。(2)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进行人工诱变生产新微生物的方法。这种类型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微生物在诱变条件下所产生的随机突变,这种突变往往是随机的,很难通过重复诱变条件而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在一定的诱变条件下必然得到具有该特性的微生物,否则不能授予专利权。
对于基因等遗传物质可否获专利保护,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许多人认为,基因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属于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在实际作法中,很多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都对基因授予专利权。它们的理由是:发现、测定并绘制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人体或动物基因,属于科学发现,但从客观存在的全长DNA序列中选择特定的片段,第一次用技术的手段将其分离出来或克隆出来,使其产生一定的应用价值,这就应该是一种技术发明。在我国,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5条和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10章的相应规定,存在于自然界的未经人类的任何技术处理的遗传物质,属于科学发现的范畴,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经特定的分离、筛选或培养技术得到的有工业应用价值的可重复获得的遗传物质,可以得到专利保护。
另外,还有围绕着在TRIPs协定中特定术语的定义的争论,如“微生物”、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有效专门制度”(sui generis)的含义等等。在欧洲、美国、日本均已用“生物材料”替代“微生物”这一概念,并且对术语“生物材料”下了定义:“任何含有遗传信息并能够自身复制或在生物系统中被复制的材料。”根据这一定义,生物材料包括了动物、植物、微生物、细菌、质粒和基因等。这样,以后将有可能出现需要为专利申请保藏动物或植物的情况,这就为专利行业及现有的微生物菌种保藏单位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于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有效专门制度”的问题,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b项提到:“……但成员应以专利制度或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给植物新品种以保护,……”这一“有效专门制度”是什么?它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关系如何?以及它与TRIPs协议的关系又怎样?它如何与《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相协调?这些都是亟需解决与处理的问题。
对于人类基因序列方面的资料是否有资格获取专利,有不同的观点。在有些国家,有些公司已经就人类基因资料申请并获得了专利。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授予转基因的蛋白质或DNA以专利,转基因蛋白质是一些新疫苗里的关键的活性成分,生产商通常对疫苗生产过程拥有专利,而不对疫苗中的化学产品本身拥有专利。如果对转基因产品给予专利保护,将会使一个本来已经很狭小的疫苗生产市场域,因为限制了竞争而导致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公共健康危机。
WTO内的CTE(WTO中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和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委员会讨论了生物技术发明可否给予专利问题。TRIPs委员会的讨论主要围绕TRIPs协议第27条第3款(b)项进行。
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会极大地增进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质,因此,会增加农产品市场供给,降低农产品价格。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绿色革命”就是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典范。正是依靠以先进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和化肥、现代灌溉技术的引入为特征的绿色革命,亚太地区极大地改善了本地区的食物供应,使大批人口解决了吃饭问题,基本避免了历史上长期困扰该地区的大饥荒威胁。
然而,现代生物技术在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有巨大的危险性。有关生物技术的安全和潜在的危害虽然没有得到有力的科学论证,但是学界对它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事实上,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遗传工程生物都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就利用科学合作的方式,将本国禁止或者有可能危害到生态环境以及本国民众感情的科学实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去做。例如,克隆人研究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出于一些伦理和法律上的考虑被法律禁止,于是,一些科学家就将这项研究转移到拉丁美洲或非洲一些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去做,以此逃避法律的规约和制裁。
对转基因产品贸易,各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各种不同立场,在《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和77国集团等国家在转基因产品的越境转移上坚持“预防为主”原则。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和乌拉圭6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组成了“迈阿密集团”,他们希望在转基因产品上实行自由贸易。欧盟及一些国家与意见一致集团的观点相似,主张预防为主原则;同时,这些国家国内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因而该集团倾向于扩大《议定书》的调整范围。另两个集团是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组成的“和事集团”及中东欧组成的中间路线集团。
以迈阿密集团为主的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对转基因产品贸易持肯定观点。在转基因产品安全方面,他们认为,从转基因产品的研究开发、种植、加工到销售都有严格的安全评估程序,其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因此,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在贸易方面,坚持转基因产品的出口无须经过进口国的批准。为了保证转基因产品出口不受限制,他们宣传转基因产品是安全可靠的,努力维护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信心。
由欧盟、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转基因产品进口国对转基因产品贸易持否定态度。在安全性方面,他们担心转基因产品可能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持谨慎态度。在贸易方面,极力主张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和坚持利用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来设置贸易壁垒,限制美国等国家农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另外,对转基因产品发展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一些国际性环保组织,他们认为,转基因产品的普及,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进一步扭曲。
而且,各国和区域性组织对转基因产品的检验和风险评估制度差别极大。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粮农组织正在致力于改进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制度和国际规则。1999年在巴黎成立了生物技术安全网,目标是分享信息,促进生物技术安全领域内政府间的合作。
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是加剧各国转基因产品贸易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WTO下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协议》(SPS)要求各成员国透明各自的危险评估标准和方法,但是,由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目前还没有一致、充分的科学证据,缺乏国际统一标准,各国只能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标准,因此各国披露的危险评估标准和方法不可能建立在公认的科学基础之上,分歧当然不可避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作出努力,制定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方面所需的变化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规则。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生物技术安全机构间网络IANB(Inter-Agency Network for Safety in Biotechnology),它的目标是分享信息,促进政府机构间的与生物技术安全有关的合作。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转基因问题、可能蔓延到环境中去的转基因种籽问题与SPS(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有关。SPS委员会就生物安全议定书谈判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还讨论了透明度问题、国际标准的发展问题、对与转基因有关的产品进行通报的问题,以及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果没有通报,WTO应采取的措施等问题。另外,在继续进行的农业谈判中,也提出了一个中心原则的建议,即要确保涉及“新技术”产品的贸易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可预测的和及时的。然而,这些建议都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讨论。
2000年1月通过的《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议定书)是目前最重要的处理转基因产品的国际法律规则。由于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全有负面影响,对保护人类健康有风险,因此,议定书的目标定位于保证其跨国转移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根据《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各国政府有权出于保护公共健康和保护环境的理由,禁止进口活的基因饰变生物(LMO),以防止如转基因生物种子通过种植或者其他方式进入本国环境。所谓基因饰变生物,是转基因产品(GMO)的一种,特别指未经加工过的转基因产品如种子等。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问题上,《议定书》的重要规定还有:进口方的事先知情与同意。是否同意进口,可能仍然维持风险预防原则,而不是采取一般问题上的科学证据原则。进口方如果不同意基因饰变生物进口,不必证明其对健康和环境有不利影响,即不负举证责任。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在环境保护和国际法上都意义重大,无疑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不倾向于保护贸易和商业利益。对于含有基因饰变生物成分,但是直接用于消费或者进一步加工的转基因产品,要求则较低,但是,基本的原则与对基因饰变活生物体的要求是一致的,即进口国的事先知情以及可以采用风险预防原则。
《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有关文件既有互相支持、补充的方面,也有相互不一致的地方。举例说明,根据《议定书》,要出口活基因饰变产品如种子的国家需在事先装运前征得进口国的同意,这是法律义务。在某些情况下,进口国可以要求出口国出具风险评估报告。而根据WTO中的SPS协议,是进口方义务,进口方如果对产品(包括转基因产品)采取任何禁止或者限制进口措施,它有义务证明其措施的合理性、合法性,即其措施有科学证据支持,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如果发生此类纠纷被提交到WTO,其争端解决机制当然会根据SPS来裁决。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是《议定书》的成员方,相信也会考虑《议定书》的规定。
(一)SPS对生物技术产品贸易的安排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anitary and Phytosantitary Measures,简称SPS)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防止以保护主义名义滥用SPS措施。按照SPS的宗旨,缔约各方“为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目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要符合三条原则。
1.科学证据原则。SPS规定,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第2条);各成员所采取的SPS措施应以科学原理为依据,而且这样的科学依据标准应该不断的进步;各成员国采取的SPS措施可以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但这些SPS措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第3条)。这一规定有两层含义:其一,SPS允许各国根据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特性来决定可承受的风险程度,自行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但这些标准和规则要以科学原理为依据。其二,一国可以实施比国际标准高的标准,条件是能有适当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些标准是合理的。换句话说,虽然SPS协定明确允许WTO成员建立自己的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标准,但它要求该措施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上。但是,基因技术的现状是短期内还无法就该技术的长期影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法做出符合要求的风险评估报告。以美国与欧盟之间激素牛肉案为例,美国引用SPS协定,提出欧盟对激素饲料饲养的牲畜的肉及肉类制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与欧盟的WTO义务相冲突,根据就是欧盟不能出具该肉类制品对健康具有威胁的科学风险评估证据。
2.风险评估和适度保护原则。SPS允许各国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可承受危险程度,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同时还需考虑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第5.1条)。在风险评估时,各成员应考虑可获得的科学证据、加工和生产方法、相关生态和环境条件因素等(第5.2条)。SPS协议规定,为了将保护措施对贸易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成员国应该在考虑有关风险评估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可接受的危险水平,并据此做出本国的适度保护水平(第5.4条)。
3.国际协调原则。从本质上,SPS的目标是通过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国际标准,从而达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SPS措施的目的。SPS要求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应该依据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第3.1条),并应尽可能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附属机构,以促进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调。这些组织包括保护食品安全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保护动物健康的国际兽医组织(OIE)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第12.3条)。SPS认为,如果成员国采用国际标准,那么就可将该国SPS措施视为符合SPS的科学依据要求(第3.2条)。
虽然各成员国已经同意在制定SPS国际标准方面进行合作,一些国际组织在中间也发挥了协调作用,但由于制定国际标准的速度太慢,还很难跟上生物技术产品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如果成员国采取的措施高于现行国际标准,那么该国必须承担证明该措施合理性的责任,即它必须能够证明该措施有“科学证据”(第5.1条)。同时,即使成员国能够证明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还必须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第5.4条)。这也就是说,现有的SPS协议框架下,欧盟的谨慎原则是不成立的,而与美国的要求基本一致。同时,协议还规定:“当成员处于疾病传播的危急时刻,但又缺乏科学依据时,允许暂时适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作为预防步骤。”显然,SPS协议又在缺乏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赋予了成员国短期内限制转基因产品进口的权利。欧盟自然可以根据这一规定改变目前不利的局势,可以预见,欧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将继续深化。
(二)TBT对生物技术产品贸易的安排
技术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是指一些国家或组织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维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采取的技术法规、标准、认证等技术性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构成了壁垒。根据TBT协议规定,成员国在实施上述强制性产品标准时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基于TBT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贸易造成影响,因此各成员国在采取TBT措施时要遵循下列原则。
1.尽量采用国际标准。TBT敦促各国政府朝着使用国际标准的方向努力。TBT第2.4条责成成员国使用现存的国际标准,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的无效或不适当。合法目的包括“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政府还必须确保标准化机构遵守《良好行为规范准则(the Code Good Practice)》。该准则是TBT协议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指导成员国政府标准化机构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准则(第4条)。
2.合理的TBT措施成本。TBT规定,标签的成本一般应与制定该标签的目的相符,即产品标签的成本不应过分加重生产者的负担和影响消费者从标签上获得的利益。各国对标签、包装都有详细的规范,这些规范有些是必需的,但也有些国家认为这些TBT措施大大增加了出口商的成本,有些特殊的要求难以做到。此外,食品转基因成分检测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费用过高,一般出口商难以承受。由于各国检验标准、方式不统一以及工作效率低,甚至是人为的破坏、阻挠都可能会造成贸易技术壁垒。
3.产品标识管理体制。WTO成员国之间已有有关生物技术产品标识问题的争论。1998年,欧盟向TBT委员会提出了实施转基因产品强制标识制度。欧盟的理由是含有基因改变的DNA或蛋白质的食品和食品成分与传统同类产品不同,因此,必须标识并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美国认为欧盟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转基因产品与传统方法生产的产品木具有实质等同性,如果本质特征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不应该仅仅依据生产方法而对产品贴加标签。美国等转基因产品出口国认为,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在成分、质量、安全方面与利用其他育种方法生产的产品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转基因标识管理体制要符合TBT的精神,尽量采用国际标准。但是,根据目前在WTO框架下多边协商的进展来看,TBT在其后续管理过程中是否能够解决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仍然有待观察。如果WTO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将可能对其解决以后可能产生的、是以生产过程为基础还是以产品特征为基础进行产品标识管理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技术产品的贸易问题上,可能适用TBT协议,也可能适用SPS协议。其区别在于争端的起因是否基于人类的健康考虑。如果在食品问题上,出于人体健康问题而限制添加剂的使用,则属于SPS协议的管辖范围。如果采取的措施是出于保持食品成分的完整性,则适用TBT协议。其管理范围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SPS协议对成员国的要求标准更高一些:SPS协议要求SPS措施要以科学为根据,而TBT协议仅仅要求缔约国采取的TBT措施符合协议目的并且依照有关国际标准制定即可(TBT协议第2.5款)。
因为当前对生物技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方面,因此,在WTO框跄谟泄厣锛际醪返拿骋孜侍庵饕Ω檬视肧PS协议。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 TRIPs)是一项管理知识产权的重要国际立法体系。其宗旨是确保WTO成员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产品有最低限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社会,转基因活生物体及其产品已经是多种知识产权的保护主题,如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和商业秘密等。
根据TRIPs协议规定:一切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发明或是方法发明,只要其新颖、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均应有可能获得专利(第27.1条)。但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德,成员国可以排除某些发明于专利保护之外(第27.2条)。还有,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的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但要求成员国给植物品种以专利或其它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加以保护(第27.3b条)。
TRIPs协议没有特别提到基因或基因技术专利权问题,成员国似乎可以对此作出如下解释:某一经过基因工程修饰过的基因可能是新的、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显然,该基因符合TRIPs协议中有关发明的条件,可以作为一项发明赋予专利权,受TRIPs协议保护。虽然TRIPs协议中排除专利保护条款包括“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但基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物体。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基因和生命形式有关就拒绝对其进行专利保护。或许可以借助用公共秩序和公德条款来拒绝对基因予以专利保护。但很难说这是否符合TRIPs规定,比如某一基因,可以使大米富含丰富的维他命,但是如果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该基因或是该种大米对人类健康或者环境具有损害,那么就不能以此为依据拒绝授予其专利权。如何在WTO框架内对生物技术产品及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WTO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生物技术让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但生物技术不仅改造着世界,也改造着人类自身。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引起伦理道德及社会问题,甚至给人类的健康带来灾难性影响。我们必须设计一种良好的法律制度来引导生物技术的发展,从而让我们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该问题决不是各国“专利法”及其他知识产权法本身所能完全解决的,需要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成员还可以将下列各项排除于可获专利之外;除微生物之处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是生物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但成员应以专利制度或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给植物新品种以保护。对本项规定应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的4年之后进行检查。
胡奕,兰小筠.浅论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J].湖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何建军,胡隆菊,王国华.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几个问题[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3).
WTO ARREEMENTS&PUBLIC HEALTH[Z].printed by the WTO Secretariat,2002.130.
Sean D.Murphy.Bio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Law[M].42 Harv.Int’l L.J.2001.471
生物技术也称生物工程,它以生命科学和技术的理论与成就为基础,将之应用于生物体的生长与加工过程,有目的地对生物体进行控制和作用,从而提供人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近20年来,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和成果,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疾病诊断、治疗、预防方法和新的医药。人类基因的解码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新高峰,生物技术可能会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医学进步的新时代。生物技术的运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从人类到动物,从基因到病毒,从植物到树种,都已经为生物技术所涉足。生物技术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逐渐显露,相应的法律问题也提了出来。
药品的专利问题一向有争论,生物技术产品专利问题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核心问题是,生物技术产品是否有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即,它是否符合申请专利所需要的三个基本原则:实用性、新颖性、创造性。对生物技术与专利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人体基因、生命形式是否属于科学发现
由于专利法规定科学发现不能授予专利权,因此,即使在欧美及日本也有人认为,微生物和人体基因等遗传物质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属于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前联邦德国最高法院1975年的判例“酵母”所涉及的专利申请在联邦专利法院就曾被驳回,理由是所申请保护的微生物自地球上有生物以来就有,属于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联邦最高法院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对其可以有计划地利用。生物自然力获得有因果关系的结果也是技术方案,发明如果能提供一种可仿制地生产微生物的方法,则可以对该微生物授予专利。又如,欧洲专利局1994年的异议审查决定“松弛素”所涉及的人体蛋白编码DNA片段即被异议人认为是已经存在的天然物质,属于科学发现,要求撤销其专利权。而异议审查小组则认为,分离和表达人体蛋白编码DNA片段不是发现,所申请的DNA片段是有具体结构和用途的全新产品,因而可以授予专利权。
实际上,发明与发现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如果某专利申请仅仅揭示了某微生物菌种或人体基因的客观存在,应当认为是一种科学发现;而如果能够首次将其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使其具有应用价值,则应当认定为一项发明。这样做,与专利法规对于其它天然物质的规定是一致的。仅仅发现了某一天然物质的存在属于科学发现,是不能授予专利权的;而通过技术手段第一次将其分离出来,改变了其存在状态或内部结构,从而使其显示出过去未曾显示的使用价值,就可以视为一项发明,可以依法授予专利权。现在,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都认为,人体基因是可以依法授予专利权的。
(二)伦理道德标准问题
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利法律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判断标准越来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例如,在欧洲专利局的“哈佛鼠”一案中,就多次涉及伦理道德的标准问题。在欧洲专利局异议审查合议组的公开审理中,异议人多次指出,用动物作试验和折磨动物是不道德的;而且,带有癌基因的动物一旦从实验室跑出,就会对环境造成无法控制的污染,严重地妨害公共利益。而专利权人却辩解,其发明可以减少受试动物的数量,从而从总体上减轻动物的痛苦,且高效地用于研究和开发治疗癌症的药物是为了免除人类的痛苦,保证人类的健康,因而是道德的。合议组则认为,应当综合权衡发明可能带来的害处和危险与发明的益处和优点的关系;本发明的益处是无可争议的,不能由于技术危险就不授予专利;控制危险技术的使用不是专利局的任务,而是其它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然而,伦理道德标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各国宪法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又涉及民法通则关于人只能作为法律主体,而不能作为客体的原则。伴随生物技术的日益发展,许多有关生命伦理学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暴露。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对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已不再是什么科幻电影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而且,人类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比如致癌化合物、杀虫剂(如DTT)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其它产品,它们都是难以纠正的灾难的根源。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人类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也承担着如何使人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另外,伦理道德标准还涉及民族、宗教、社会及文化等诸多方面,这无疑已远远超出了专利法所能涉及的范围。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应当通过国家及全社会来逐步加以解决。
(三)关于动物和植物品种的概念问题
由于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其传统生物学的繁殖往往难以保持可重复性,因此,多数国家的专利法都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然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尤其是DNA重组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各种转基因动物或转基因植物,这是立法者当时未能预料的。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植物的出现,已经从技术上克服了这种缺陷,从而对这种法律规定提出了挑战。1990年,欧洲专利局申诉委员会对“哈佛鼠”一案所做出的决定中,对“品种”一词做出了狭义的解释,将其等同于动物分类学“种”的概念,曾经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于植物品种这一概念,其解释也出现了混乱。例如,虽然欧洲专利公约和德国专利法都有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但在审查实践中已经授予了许多植物专利。欧洲专利局申诉委员会在1988年“杂交植物”判例中,认为关于植物品种没有定义,而根据某些成员国的植物品种保护条例的定义,植物品种应有稳定性和同质性,而该申请的“杂交植物”已经改变,因而不属于植物品种,可以授予专利。在德国,凡是没有列入植物品种保护条例的植物,实际上都是可以得到专利保护的。而在欧盟1998年7月6日发布的98(44EG)号指令和欧洲专利组织管理委员会1999年6月16日根据该指令所修改的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中,又一次肯定了对动物和植物品种概念的这一解释,即:“‘植物品种’指任何一个单一已知最低级别植物学分类单位的植物群体”,“要求保护的植物或动物若不限定于一个特定的植物或动物品种,就是可以授予利的主题”。
(四)关于生物体的保护问题
有关生物体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直是西方许多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它有时成为一项判决能否成立、一项立法能否通过的关键所在。分析这些国家的判例和立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问题的实质是人体及人体的部分(器官)是否可以享有独占权。目前看来,美国自Allen案后,美国专利局有关动物专利的《通告》以及哈佛转基因鼠在美国获得动物专利,随后又获得欧洲专利,以及美国《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法》议案、欧共体《理事会指令》对动物、植物,甚至动物和植物品种获得专利保护都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同时他们的判例和立法中都明确禁止人体及人体的部分获得专利权。人体本身不应获得专利权看来不存在太大的争议,问题是人体的部分应当包括多大的范围?是人体体内和体外的所有物质还是仅指人体器官?人体的部分是否也包括人类的遗传物质?从目前国外的情况看,禁止专利人体及人体的部分范围是很大的。人体的部分(parts of human body)不仅仅指人体的器官(organ of human body),而且包括人体细胞和人体遗传物质。虽然人体的部分被禁止获得专利权,但是包含人体遗传物质的生物体却有可能获得专利。比如: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合成某种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的人类DNA片断与细菌的遗传物质重组,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细菌,而这种细菌是可以获得专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转基因微生物或转基因动物享有专利权是否意味着对人体的部分也就拥有了专利权呢?另外,从技术上来讲,人类目前距有能力制造人体器官的日子也并不遥远了,这种利用生物工程技术离体制造人体器官对更换人体坏死的器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制造过程具有明显的工业生产的特征,这种离体单独制造的人体器官应当获得专利权吗?
(五)关于“微生物”的概念问题
这里所说的微生物,包括各种细菌、真菌、放线菌和病毒,动植物细胞系、质粒、原生动物和藻类。对于微生物新品种发明的专利保护,各国都已达成共识。当然,未经人类的任何技术处理而自然存在的微生物,属于专利法中所述的科学发现的范畴,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只有经过特定的分离、筛选或培养技术产生新的微生物品种,可重复获得,且具有特定的工业用途时,微生物才可以得到专利保护。此时,除该微生物新品种可获产品发明专利外,生产这种微生物的方法还可获方法发明专利。应该注意,下列两种生产新微生物方法就不能被授予专利:(1)由自然界筛选特定微生物的方法。这类方法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很大随机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重现,不具有实用性,因此,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这种方法可以重复实施,否则不能授予这种方法专利权。(2)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进行人工诱变生产新微生物的方法。这种类型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微生物在诱变条件下所产生的随机突变,这种突变往往是随机的,很难通过重复诱变条件而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在一定的诱变条件下必然得到具有该特性的微生物,否则不能授予专利权。
对于基因等遗传物质可否获专利保护,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许多人认为,基因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属于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在实际作法中,很多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都对基因授予专利权。它们的理由是:发现、测定并绘制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人体或动物基因,属于科学发现,但从客观存在的全长DNA序列中选择特定的片段,第一次用技术的手段将其分离出来或克隆出来,使其产生一定的应用价值,这就应该是一种技术发明。在我国,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5条和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10章的相应规定,存在于自然界的未经人类的任何技术处理的遗传物质,属于科学发现的范畴,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经特定的分离、筛选或培养技术得到的有工业应用价值的可重复获得的遗传物质,可以得到专利保护。
另外,还有围绕着在TRIPs协定中特定术语的定义的争论,如“微生物”、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有效专门制度”(sui generis)的含义等等。在欧洲、美国、日本均已用“生物材料”替代“微生物”这一概念,并且对术语“生物材料”下了定义:“任何含有遗传信息并能够自身复制或在生物系统中被复制的材料。”根据这一定义,生物材料包括了动物、植物、微生物、细菌、质粒和基因等。这样,以后将有可能出现需要为专利申请保藏动物或植物的情况,这就为专利行业及现有的微生物菌种保藏单位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于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有效专门制度”的问题,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b项提到:“……但成员应以专利制度或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给植物新品种以保护,……”这一“有效专门制度”是什么?它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关系如何?以及它与TRIPs协议的关系又怎样?它如何与《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相协调?这些都是亟需解决与处理的问题。
对于人类基因序列方面的资料是否有资格获取专利,有不同的观点。在有些国家,有些公司已经就人类基因资料申请并获得了专利。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授予转基因的蛋白质或DNA以专利,转基因蛋白质是一些新疫苗里的关键的活性成分,生产商通常对疫苗生产过程拥有专利,而不对疫苗中的化学产品本身拥有专利。如果对转基因产品给予专利保护,将会使一个本来已经很狭小的疫苗生产市场域,因为限制了竞争而导致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公共健康危机。
WTO内的CTE(WTO中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和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委员会讨论了生物技术发明可否给予专利问题。TRIPs委员会的讨论主要围绕TRIPs协议第27条第3款(b)项进行。
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会极大地增进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质,因此,会增加农产品市场供给,降低农产品价格。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绿色革命”就是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典范。正是依靠以先进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和化肥、现代灌溉技术的引入为特征的绿色革命,亚太地区极大地改善了本地区的食物供应,使大批人口解决了吃饭问题,基本避免了历史上长期困扰该地区的大饥荒威胁。
然而,现代生物技术在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有巨大的危险性。有关生物技术的安全和潜在的危害虽然没有得到有力的科学论证,但是学界对它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事实上,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遗传工程生物都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就利用科学合作的方式,将本国禁止或者有可能危害到生态环境以及本国民众感情的科学实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去做。例如,克隆人研究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出于一些伦理和法律上的考虑被法律禁止,于是,一些科学家就将这项研究转移到拉丁美洲或非洲一些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去做,以此逃避法律的规约和制裁。
对转基因产品贸易,各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各种不同立场,在《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和77国集团等国家在转基因产品的越境转移上坚持“预防为主”原则。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和乌拉圭6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组成了“迈阿密集团”,他们希望在转基因产品上实行自由贸易。欧盟及一些国家与意见一致集团的观点相似,主张预防为主原则;同时,这些国家国内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因而该集团倾向于扩大《议定书》的调整范围。另两个集团是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组成的“和事集团”及中东欧组成的中间路线集团。
以迈阿密集团为主的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对转基因产品贸易持肯定观点。在转基因产品安全方面,他们认为,从转基因产品的研究开发、种植、加工到销售都有严格的安全评估程序,其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因此,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在贸易方面,坚持转基因产品的出口无须经过进口国的批准。为了保证转基因产品出口不受限制,他们宣传转基因产品是安全可靠的,努力维护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信心。
由欧盟、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转基因产品进口国对转基因产品贸易持否定态度。在安全性方面,他们担心转基因产品可能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持谨慎态度。在贸易方面,极力主张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和坚持利用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来设置贸易壁垒,限制美国等国家农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另外,对转基因产品发展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一些国际性环保组织,他们认为,转基因产品的普及,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进一步扭曲。
而且,各国和区域性组织对转基因产品的检验和风险评估制度差别极大。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粮农组织正在致力于改进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制度和国际规则。1999年在巴黎成立了生物技术安全网,目标是分享信息,促进生物技术安全领域内政府间的合作。
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是加剧各国转基因产品贸易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WTO下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协议》(SPS)要求各成员国透明各自的危险评估标准和方法,但是,由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目前还没有一致、充分的科学证据,缺乏国际统一标准,各国只能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标准,因此各国披露的危险评估标准和方法不可能建立在公认的科学基础之上,分歧当然不可避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作出努力,制定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方面所需的变化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规则。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生物技术安全机构间网络IANB(Inter-Agency Network for Safety in Biotechnology),它的目标是分享信息,促进政府机构间的与生物技术安全有关的合作。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转基因问题、可能蔓延到环境中去的转基因种籽问题与SPS(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有关。SPS委员会就生物安全议定书谈判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还讨论了透明度问题、国际标准的发展问题、对与转基因有关的产品进行通报的问题,以及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果没有通报,WTO应采取的措施等问题。另外,在继续进行的农业谈判中,也提出了一个中心原则的建议,即要确保涉及“新技术”产品的贸易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可预测的和及时的。然而,这些建议都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讨论。
2000年1月通过的《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议定书)是目前最重要的处理转基因产品的国际法律规则。由于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全有负面影响,对保护人类健康有风险,因此,议定书的目标定位于保证其跨国转移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根据《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各国政府有权出于保护公共健康和保护环境的理由,禁止进口活的基因饰变生物(LMO),以防止如转基因生物种子通过种植或者其他方式进入本国环境。所谓基因饰变生物,是转基因产品(GMO)的一种,特别指未经加工过的转基因产品如种子等。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问题上,《议定书》的重要规定还有:进口方的事先知情与同意。是否同意进口,可能仍然维持风险预防原则,而不是采取一般问题上的科学证据原则。进口方如果不同意基因饰变生物进口,不必证明其对健康和环境有不利影响,即不负举证责任。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在环境保护和国际法上都意义重大,无疑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不倾向于保护贸易和商业利益。对于含有基因饰变生物成分,但是直接用于消费或者进一步加工的转基因产品,要求则较低,但是,基本的原则与对基因饰变活生物体的要求是一致的,即进口国的事先知情以及可以采用风险预防原则。
《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有关文件既有互相支持、补充的方面,也有相互不一致的地方。举例说明,根据《议定书》,要出口活基因饰变产品如种子的国家需在事先装运前征得进口国的同意,这是法律义务。在某些情况下,进口国可以要求出口国出具风险评估报告。而根据WTO中的SPS协议,是进口方义务,进口方如果对产品(包括转基因产品)采取任何禁止或者限制进口措施,它有义务证明其措施的合理性、合法性,即其措施有科学证据支持,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如果发生此类纠纷被提交到WTO,其争端解决机制当然会根据SPS来裁决。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是《议定书》的成员方,相信也会考虑《议定书》的规定。
(一)SPS对生物技术产品贸易的安排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anitary and Phytosantitary Measures,简称SPS)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防止以保护主义名义滥用SPS措施。按照SPS的宗旨,缔约各方“为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目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要符合三条原则。
1.科学证据原则。SPS规定,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第2条);各成员所采取的SPS措施应以科学原理为依据,而且这样的科学依据标准应该不断的进步;各成员国采取的SPS措施可以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但这些SPS措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第3条)。这一规定有两层含义:其一,SPS允许各国根据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特性来决定可承受的风险程度,自行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但这些标准和规则要以科学原理为依据。其二,一国可以实施比国际标准高的标准,条件是能有适当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些标准是合理的。换句话说,虽然SPS协定明确允许WTO成员建立自己的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标准,但它要求该措施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上。但是,基因技术的现状是短期内还无法就该技术的长期影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法做出符合要求的风险评估报告。以美国与欧盟之间激素牛肉案为例,美国引用SPS协定,提出欧盟对激素饲料饲养的牲畜的肉及肉类制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与欧盟的WTO义务相冲突,根据就是欧盟不能出具该肉类制品对健康具有威胁的科学风险评估证据。
2.风险评估和适度保护原则。SPS允许各国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可承受危险程度,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同时还需考虑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第5.1条)。在风险评估时,各成员应考虑可获得的科学证据、加工和生产方法、相关生态和环境条件因素等(第5.2条)。SPS协议规定,为了将保护措施对贸易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成员国应该在考虑有关风险评估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可接受的危险水平,并据此做出本国的适度保护水平(第5.4条)。
3.国际协调原则。从本质上,SPS的目标是通过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国际标准,从而达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SPS措施的目的。SPS要求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应该依据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第3.1条),并应尽可能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附属机构,以促进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调。这些组织包括保护食品安全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保护动物健康的国际兽医组织(OIE)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第12.3条)。SPS认为,如果成员国采用国际标准,那么就可将该国SPS措施视为符合SPS的科学依据要求(第3.2条)。
虽然各成员国已经同意在制定SPS国际标准方面进行合作,一些国际组织在中间也发挥了协调作用,但由于制定国际标准的速度太慢,还很难跟上生物技术产品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如果成员国采取的措施高于现行国际标准,那么该国必须承担证明该措施合理性的责任,即它必须能够证明该措施有“科学证据”(第5.1条)。同时,即使成员国能够证明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还必须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第5.4条)。这也就是说,现有的SPS协议框架下,欧盟的谨慎原则是不成立的,而与美国的要求基本一致。同时,协议还规定:“当成员处于疾病传播的危急时刻,但又缺乏科学依据时,允许暂时适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作为预防步骤。”显然,SPS协议又在缺乏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赋予了成员国短期内限制转基因产品进口的权利。欧盟自然可以根据这一规定改变目前不利的局势,可以预见,欧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将继续深化。
(二)TBT对生物技术产品贸易的安排
技术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是指一些国家或组织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维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采取的技术法规、标准、认证等技术性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构成了壁垒。根据TBT协议规定,成员国在实施上述强制性产品标准时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基于TBT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贸易造成影响,因此各成员国在采取TBT措施时要遵循下列原则。
1.尽量采用国际标准。TBT敦促各国政府朝着使用国际标准的方向努力。TBT第2.4条责成成员国使用现存的国际标准,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的无效或不适当。合法目的包括“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政府还必须确保标准化机构遵守《良好行为规范准则(the Code Good Practice)》。该准则是TBT协议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指导成员国政府标准化机构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准则(第4条)。
2.合理的TBT措施成本。TBT规定,标签的成本一般应与制定该标签的目的相符,即产品标签的成本不应过分加重生产者的负担和影响消费者从标签上获得的利益。各国对标签、包装都有详细的规范,这些规范有些是必需的,但也有些国家认为这些TBT措施大大增加了出口商的成本,有些特殊的要求难以做到。此外,食品转基因成分检测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费用过高,一般出口商难以承受。由于各国检验标准、方式不统一以及工作效率低,甚至是人为的破坏、阻挠都可能会造成贸易技术壁垒。
3.产品标识管理体制。WTO成员国之间已有有关生物技术产品标识问题的争论。1998年,欧盟向TBT委员会提出了实施转基因产品强制标识制度。欧盟的理由是含有基因改变的DNA或蛋白质的食品和食品成分与传统同类产品不同,因此,必须标识并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美国认为欧盟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转基因产品与传统方法生产的产品木具有实质等同性,如果本质特征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不应该仅仅依据生产方法而对产品贴加标签。美国等转基因产品出口国认为,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在成分、质量、安全方面与利用其他育种方法生产的产品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转基因标识管理体制要符合TBT的精神,尽量采用国际标准。但是,根据目前在WTO框架下多边协商的进展来看,TBT在其后续管理过程中是否能够解决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仍然有待观察。如果WTO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将可能对其解决以后可能产生的、是以生产过程为基础还是以产品特征为基础进行产品标识管理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技术产品的贸易问题上,可能适用TBT协议,也可能适用SPS协议。其区别在于争端的起因是否基于人类的健康考虑。如果在食品问题上,出于人体健康问题而限制添加剂的使用,则属于SPS协议的管辖范围。如果采取的措施是出于保持食品成分的完整性,则适用TBT协议。其管理范围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SPS协议对成员国的要求标准更高一些:SPS协议要求SPS措施要以科学为根据,而TBT协议仅仅要求缔约国采取的TBT措施符合协议目的并且依照有关国际标准制定即可(TBT协议第2.5款)。
因为当前对生物技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方面,因此,在WTO框跄谟泄厣锛际醪返拿骋孜侍庵饕Ω檬视肧PS协议。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 TRIPs)是一项管理知识产权的重要国际立法体系。其宗旨是确保WTO成员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产品有最低限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社会,转基因活生物体及其产品已经是多种知识产权的保护主题,如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和商业秘密等。
根据TRIPs协议规定:一切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发明或是方法发明,只要其新颖、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均应有可能获得专利(第27.1条)。但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德,成员国可以排除某些发明于专利保护之外(第27.2条)。还有,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的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但要求成员国给植物品种以专利或其它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加以保护(第27.3b条)。
TRIPs协议没有特别提到基因或基因技术专利权问题,成员国似乎可以对此作出如下解释:某一经过基因工程修饰过的基因可能是新的、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显然,该基因符合TRIPs协议中有关发明的条件,可以作为一项发明赋予专利权,受TRIPs协议保护。虽然TRIPs协议中排除专利保护条款包括“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但基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物体。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基因和生命形式有关就拒绝对其进行专利保护。或许可以借助用公共秩序和公德条款来拒绝对基因予以专利保护。但很难说这是否符合TRIPs规定,比如某一基因,可以使大米富含丰富的维他命,但是如果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该基因或是该种大米对人类健康或者环境具有损害,那么就不能以此为依据拒绝授予其专利权。如何在WTO框架内对生物技术产品及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WTO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生物技术让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但生物技术不仅改造着世界,也改造着人类自身。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引起伦理道德及社会问题,甚至给人类的健康带来灾难性影响。我们必须设计一种良好的法律制度来引导生物技术的发展,从而让我们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该问题决不是各国“专利法”及其他知识产权法本身所能完全解决的,需要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成员还可以将下列各项排除于可获专利之外;除微生物之处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是生物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但成员应以专利制度或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给植物新品种以保护。对本项规定应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的4年之后进行检查。
胡奕,兰小筠.浅论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J].湖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何建军,胡隆菊,王国华.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几个问题[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3).
WTO ARREEMENTS&PUBLIC HEALTH[Z].printed by the WTO Secretariat,2002.130.
Sean D.Murphy.Bio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Law[M].42 Harv.Int’l L.J.2001.471
本文只供参考
联系邮箱:kefu@labbase.net
版权与免责声明
- 凡本网注明“来源:来宝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来宝网,转载请必须注明来宝网, //www.next-search.com,违反者本网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 本网转载并注明自其它来源的作品,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转载时,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作品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 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作品发表之日起一周内与本网联系,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